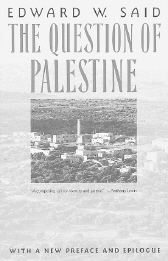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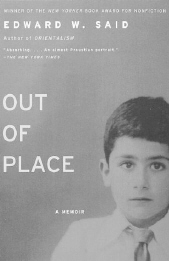
上接12月6日第71期《国际文化》
罗丝: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听起来有些无关紧要,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你。为什么你在论著中很少提到女性?你的灵感全是来自一些男性作家,例如维柯、奥尔巴赫(Auerbach)、斯皮泽(Spitzer)。你曾经对塔希娅·卡里奥卡(TahiaCarioca)的肚皮舞作过研究,我为此很感欣慰。可是,你是否也从某些女作家那儿汲取过创作灵感?简·奥斯丁和乔治·爱略特显然不在话下,因为利维斯(F.R.Leavis)把她们列入了伟大传统。
赛义德:所以,你就觉得我一定也受她们影响。
罗丝:不,不是一定。可是你能谈谈吗?你知道的,我很仰慕你,别让我失望。
赛义德:你刚才提到了塔希娅·卡里奥卡,她对我早年的生活产生过影响。哦,不,在某种意义上,我不太喜欢她。我开个名单,列举一些我欣赏的女权主义者……。
罗丝:不,不要开名单,这不能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想听你说说为什么你在论著中很少提到女性,是否与你接受的教育有关?
赛义德:哦,这是当然的。别忘了,这是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在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我知道的唯一女作曲家是克拉拉·舒曼(ClaraSchumann),她为电影《难忘的旋律》配乐。去年在纽约举办的电影节上,我还把这部电影推荐给了大家。
我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所去的学校都是男生学校———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这得怪英国的教育体制———那种学校培养了一种非常男性化的气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时,不管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哈佛,我所处的环境里既没有女大学生,也没有女教授。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位知名女学者是贾奎琳·罗米利(JacquelinedeRomilly),她是法国大学的古典主义学者。后来,我努力在这方面对自己进行教育,通过阅读妇女作家就妇女问题撰写的文章努力了解妇女的历史,但这种努力可能为时已晚。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个人经验、生活中那些让我感觉良好的时刻,以及我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受制于男性经验。
罗丝:最后一个问题。你在英国剑桥大学作了一次关于燕卜荪的讲座,题目是“歌剧中的越界与权威”。我有幸能在法国学院聆听了这一系列讲座中的第一个。你谈到了莫扎特,说他洞察到人类的本性是“千变万化、游离不定,但又没有明显特质”;他发现“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成规以及稳定的婚姻实际上并不适应人类,因为生活本身既难以捉摸又充满变化”。你的意思仿佛是,莫扎特对死亡的理解使他超越虚荣、看破虚伪、挣脱规范和传统的束缚。这些听上去令人感动、使人振奋的观点似乎表明你进入了一个写作的新起点。可是,这种新的观察角度与你的政治视野,以及与你对未来的希冀存在着何种联系?
赛义德:我觉得关系不大,但它确是我的一种感悟。之所以有这么一种感受———毫不避讳地说———是因为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感觉到了濒临死亡的压力。因此,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强烈感受,也不管这种临近终极的感觉是停留在何种意义上的,我觉得莫扎特的描述是准确的。它像一团不断变化、无法辨认的东西,汹涌澎湃地朝着我们的前方运动、变化。这几乎是叔本华式的感悟。是我目前正在着手写作的一部分内容。我还想讲最后一点———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关于身份问题的讨论:身份问题在60年代的美国曾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现在这一讨论的热点移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地区,人们觉得应该关注与自身相关的一些问题,探询自己来自哪儿,追根溯源地寻找自己的祖先———就像小说《根》以及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描述的那样。而这一切在我看来无关宏旨,令人生厌。从某种角度看,我认为身份问题是当前所有问题中最次要的。比这更重要的事是要超越身份界限,走向别处,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或许是死亡。也许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意识境界,它将有助于人们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与他者发生联系。也许仅仅是一种遗忘;在某种意义上,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必要———忘却。
罗丝:谢谢。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我们就谈到这儿,下面还有一些问题。还是让我开始吧。美国一直在为以色列提供经济援助,你对此作何种解释?习惯上,人们总是从安全防御的角度去理解美国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大规模投资。
赛义德:我认为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动因。近年来,特别是冷战以后,美国十分注重安全防御。现在,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这足以见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眼光。以色列备有精锐的空军力量,先进的核武器装备,等等,这使得美国把它当作自己在中东地区最强大的、最靠得住的战略伙伴。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道理是明摆着的———其实海湾战争已经证明———控制以色列就等于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虽然美国使用的石油只有极少部分来自中东,但是,对中东石油的控制使得美国在与世界工业国的关系中,例如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在战略上赢得了一种优势。所以说,军事防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与上述理由同样重要。由于诸多因素,(包括)像《旧约》上说的,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认同的关系。美国是世界上信奉宗教人数最多的国家。几年前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中有88%的人相信上帝。因此,美国人容易认同以色列人。双方都觉得有一种拓荒的使命感。如果翻开美国早期的清教文献,你会发现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要让犹太人回家,这是他们的使命。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人却将阿拉伯人,尤其是穆斯林人视作危险的异类。我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谈到了这一问题。现在的情形依然如此,甚至比以前更糟。美国人大谈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活动,事实上,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猖獗。正在丹弗受审的恐怖主义分子麦克伟是个白人,而且还是个满腔热情的爱国者,但他却害死了不少人。恐怖主义这一名词虽然不直接指涉中东国家,但却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代名词。不过,这可不包括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代表西方,代表西方文化。
最后要说的一点,也是隐含在你提的问题中的,美国国会中有一大批人支持以色列,而阿拉伯国家在这一点上则是无可比拟。美国国会中不仅听不到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声音,而且也没有人作任何努力。事实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与美国和以色列联姻。无论是从客观结果上看还是从主观愿望上讲,当今阿拉伯国家的多数首脑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利益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巴勒斯坦、摩洛哥以及海湾地区。他们觉得有必要维护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具备的强大保护力量,这一点,他们从曾受到美国保护的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国王身上就明白了。比这股支持力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犹太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大的群体。而阿拉伯人在那儿则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由此可见,正是上述各种因素使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形成了多种利益的联合。而利益的多样性又增强了彼此的联结,并且长久不衰,一年胜过一年。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结由来已久,而对此,阿拉伯国家根本无力对抗。
罗丝:有人提问:赛义德曾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批判权力机构,可是,如果有朝一日,受压迫的人们推翻了原先的权力机构,那么,到那时知识分子的批评使命是否就算大功告成,接下来的任务是否应该对权力起到一种维护作用呢?
赛义德:是的,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应该起到一种维护作用。尤其是对于一个由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后刚成立的政府而言,这种维护就显得更为重要。譬如,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推翻法国统治后的最初阶段,大家都觉得应该尽力维护一个在挣脱了长达一百三四十年殖民统治后刚刚成立的新政府。另一方面,这一胜利的代表者也需要支持。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起到维护作用。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看待后殖民国家的苦难的问题,例如阿尔及利亚、非洲撒哈拉沙漠周边国家,以及中东国家。就我个人而言,当纳塞尔刚上台时,我就是他的支持者。但是,也许问题就从这儿开始。支持什么?是无条件支持吗?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给予支持的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立场。当然,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也许有人会说挑毛病是件最容易不过的事。其实不然,你要给予支持,但同时还要努力使自己具有怀疑精神,与批判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你自己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当新政府开始滥用权力时(而这又是常有的事),你不会对自己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革命成果,我还是闭嘴吧。你会站出来,对诸多现象提出批评。这样的人历史上并不少见。对于殖民主义结束以后,或者发生革命时那短暂的过渡时刻,我们现在了解得还不够。
回到刚才提到的纳塞尔。如今70岁上下的整个一代人,在他们30岁左右时,因为说真话而被关进监狱,坐了好多年牢。他们是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国王家族统治。他们曾是革命的支持者,但他们后来对新政府进行了大胆的批评。他们对当局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声称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但却用大量的军队、秘密警察对人民进行控制。你们总是打着“为了人民利益”的幌子去解决所有问题,这在理论上也是行不通的。就是因为说了这番话,这些人就得接受惩罚。纳塞尔把成千上万的人抓进了监狱,让他们在监狱了呆了6年、7年或8年,使他们受尽折磨。诸如此类的事其实还有很多,只不过大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罢了。
罗丝:听众中有人提问:问题以奥兹(AmosOz)的比喻开始,说以色列国内各不相同的群体,像由颜色、形状各异的小块织物拼成的百家衣。接着,提问者想知道赛义德本人是否能够与如此繁杂的群体进行交流或与他们共事。此外,提问者以哈南·阿什拉维(HananAshrawi)的例子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阿什拉维最初以批评家的姿态站在巴勒斯坦政府的对立面,可是后来却和他们走到了一起,请问,你是否能够在目前的政治进程中扮演一种更积极的角色?最后,提问者表示,他不相信赛义德本人真的能像他自己今晚说的那样对现状持怀疑态度。
赛义德:阿什拉维镇压罢工,压制那些参加罢工的教师。她说那些人无权罢工。
以色列和平营的问题情况很复杂,由于时间关系,恐怕今天不可能细谈。不过,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虽然许多人在谈论和平,但和平一词的含义却是因人而异,我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当然,没有人对和平本身提出异议。谁敢反对和平?此刻,我想起了阿莫斯·奥兹,因为1993年9月奥斯陆协议签订之际,我和他都接受了采访。他先行一步,我后来才到;但我们彼此没有说话。记得他当时说的最后一点是,他认为奥斯陆协议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首次重大胜利。换言之,他认为这是以色列人为促进和平取得的伟大胜利。由此可见,这也算得上是对和平的一种理解,只不过是暂时讲和罢了。大多数工党分子,奥兹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持这种观点,而我希望看到的和平远非如此,真正的和平是平等基础上的和睦关系。以色列声称他们要和平,这当然是有意义的,对此,我能理解,也不反对。我的意思是,他们所谓的和平是赶快解决问题,一了百了。这一点,我也能理解。但那种和平并不意味着正义得到了伸张,也不表示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了个说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巴勒斯坦人就无可指责。但我们总得尊重事实,看看以色列是如何在阿拉伯土地上建造居留地。巴勒斯坦人曾在那片土地上耕耘生活,但后来却被赶走了。那些被称作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以色列史学家,像本尼·莫里斯(BennyMorris),对这类事实作了披露。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但并不等于奥兹说的,我们希望的和平是得到一个永久居住地。所以,我认为挑选伙伴必须小心谨慎,吹毛求疵。如果有人喜欢某一种话语方式,或者说愿意与X而不是Y对话,这都是正常的。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一方面却犯了大错:谁更接近强权,他们就和谁在一起。我总是对那些权力范围以外的人感兴趣———例如前面提到的沙哈克,还有莱勃维茨———这些人虽然没有大权,却有良知。此外,还必须修改选举法。
现在说说巴勒斯坦的形势,谈谈那儿发生的事。简单地说,我觉得权力已经败坏了那儿的知识分子。这里还得重复一遍,我本人对此表示理解。那儿多少年来一直处于被占领状态。事实上,这已是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占领;到今年已经30年了。那儿的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学会如何照料自己。可是,与之相伴的一个现象出现了: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只要进入了阿拉法特的权力势力范围,他们就成了权力的囚犯;为了维护自己的影响力和声誉,他们改变原来的观点;这种现象令人沮丧。不过,依我看,与其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与领导保持一致,倒不如说是为了生活,出于无奈,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他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我站在当权者的一边,但都被我拒绝了。他们说,你瞧,内塔尼亚胡也在我们这边了,你为什么还不放弃?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在为犹太复国主义帮忙。我觉得这些全是胡扯。巴勒斯坦政府先行的一切并不都是有利于巴勒斯坦国家和人民。实际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害的。以色列以法律的名义在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人身迫害,我们可以为此写报告进行控诉;巴勒斯坦也在干这种勾当,难道就应该饶恕吗?不管是谁,折磨别人总是不对的。至于你说我实际上不如我看上去那样富有怀疑精神,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罗丝:他希望你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赛义德:我已经说了,我对于两个国家这种提法不感兴趣。我觉得阿拉法特和奥斯陆会议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奥斯陆协议也没有生效。以色列建造了那么多的定居点,侵占了那么多的土地。以色列领导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些不知餍足;他们说,他们最多只能放弃约旦河西岸50%的土地。就算他们真的这么做了,那儿的定居点依然不变。隔离带还在那儿。巴勒斯坦的城市将会由于分割而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约旦河西岸50%的土地,西岸和加沙地带,是从前巴勒斯坦总面积的22%。如果拿走了50%,那么,剩下的就只有10%。这哪是什么公平交易?况且现实已经如此,又不能在地图上重新划分领土疆域。归根到底,两国人民都属于这片土地,只要翻开历史,站在从前巴勒斯坦的位置上看待这一切,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了。因此,双方都应该从对方寻找各自的伙伴,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以色列没有宪法,但巴勒斯坦也没有;我觉得双方都应该有一部宪法,对基本的人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和以色列犹太人同样的权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都应该享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想,大家应该就一些共同的权利展开讨论。
罗丝:我们就以赛义德的呼吁来结束今晚的讨论。他以雄辩的口才向大家表明,虽然联结由于历史原因而变得不可能,但对于连接的强调却具有强大的政治意义;人类应该像巨大的容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像大海一样尽可能地容纳一切。就让我们以这一蕴涵着乌托邦色彩的印象结束今晚的活动。
